阅读推荐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啦!!!
宋体; 为了解男性人群对尖锐湿疣疫苗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我们拟对男性人群展开此项调查,以为开展后期的尖锐湿疣疫苗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一般情况及对尖锐湿疣疫苗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全程采用匿名形式。调查不会对您的健康和隐私造成伤害,同时我们保证对调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问题,给予严格保密。
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红包啦!!!
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啦!!!
宋体; 为了解男性人群对尖锐湿疣疫苗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我们拟对男性人群展开此项调查,以为开展后期的尖锐湿疣疫苗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一般情况及对尖锐湿疣疫苗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全程采用匿名形式。调查不会对您的健康和隐私造成伤害,同时我们保证对调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问题,给予严格保密。
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红包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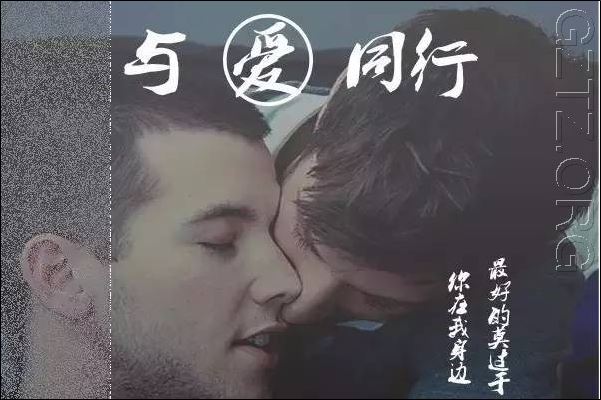 活动:与爱同行
活动:与爱同行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谈起性和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SEX-HEALTH图片大赛”正火热举行中哦!
谈起性和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SEX-HEALTH图片大赛”正火热举行中哦!
把你的想法注入到照片,图画,设计(图片或文字)与我们分享吧!
本次大赛将会给大赛前三名颁发奖励(第一名的奖励是iphone6一台,第二,三名将会有惊喜奖品)!
想了解详情请点击http://www.seshglobal.org/sex-health 《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栏目更新
- 2015-12-04青年学生染艾调查 男同性恋无套性交成传播主因
- 2015-12-04抗艾需消除同性恋者双重污名
- 2015-08-18美媒:北京东单公园为男同性恋提供安全港湾
- 2015-08-18高校教材“污名”同性恋 女生起诉获立案
- 2014-11-29【资讯】美国同性恋约炮应用Grindr的赚钱之道:寻找一夜情
- 2014-11-20【资讯】美男被性侵不愿公开 志愿者想帮忙遭拒
- 2014-11-17【资讯】广东梅毒、淋病患者去年报告数全国第一
- 2014-10-31【资讯】苹果CEO库克:身为同性恋者我感到很自豪
- 2014-10-31【资讯】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读库克的出柜文章
- 2014-10-29【资讯】台湾举行大规模同性恋游行,6.5万人参加
- 2014-10-11【资讯】爱沙尼亚通过同性恋婚姻法 允许同性恋领养小孩
- 2014-07-05【资讯】蔡明亮出书承认同性恋 自曝曾在外地猎艳
中国同性恋告别隐秘时代?
(作者或来源) 新民周刊 对中国的同性恋而言,2005年是一个节点——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大学“通识教育”阶段的沉默也被打破—— 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孙中欣博士上完《同性恋研究》的第一节课说,教室太小了,记者太多了。不无抱怨的意思。
9月7日的课程毕竟是中国第一堂关于同性恋的公开选修课,当天听课的学生和记者人数相当多。这在意料之中。倒是一个学生递条子说,哪里能找到同性恋的朋友?多少出乎她的意料。但孙中欣还是说,这是个好问题。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社会的同性恋话题都如此轻松。一墙之隔的街道其实比校园要保守得多。但这仍是历史性一刻。同性恋变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禁忌已经打破,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
转折点:2005年
“性别、性、同性恋这些都是边缘的知识,富有挑战性,容易震动学生”,孙中欣说,“能够冲击主流认识的新领域总会受到关注。”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主流认识”又是什么呢?孙中欣的同学看到她要开课,特意打来电话,他原本以为同性恋是浪漫的无性之爱,他家来自农村的保姆却告诉他,自己嫁了一个同性恋丈夫。悲剧轻而易举地清醒了他关于同性恋的浪漫想象。
城市里的男同性恋圈子里流传着一些特别的生存法则。比如说,为了掩饰身份,娶一个农村女子为妻。“对他们来说,农村女子和城市女性相比,好像不会有太多爱和感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她们常常对同性恋一无所知。”孙中欣说。
那位保姆的丈夫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但新婚妻子完全不知道“同性恋”为何物,直到面对完全无性的婚姻,并且发现丈夫另有同性的情人时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幸的是,一次偶然性行为使她怀上了丈夫的孩子。她想离婚,然而丈夫不愿意。他恨她离婚暴露了他的身份。
“除了浪漫的想象,或者彻底的无知,还有人认为‘这样的人’很少,或者认为他们很奇怪。他们从来不能想象自己的熟人中会有同性恋”,孙中欣说。1997年开始在“性别研究”课程中涉及同性恋话题以来,她已经充分领教了这种“主流认识”的模糊不清。
然而,现在形势好像发生了变化。
10年前,中国任何一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勾肩搭背的男孩子,彼此挽着胳膊的女孩子。这种亲密无间的同性身体关系,据说让西方人困惑。但这种景象好像一夜之间从大城市的街头消失了。这个细节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在孙中欣看来这是时代变化的指征:同性间过分的身体接触,现在是要冒着被疑似同性恋的危险的。
还有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播出了从艾滋病角度讨论同性恋问题的新闻专题片《以生命的名义》,几个同性恋者的面部形象正面出现在荧屏上,这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
“同性恋主动向大众暴露自己的脸,而从前,这张脸是被遮蔽的”,主动公开了同性恋身份的周丹说,“这是一个象征。”
谈话让周丹兴奋,以至会发生轻微的口吃。这个小个子的律师语速很快,声音越来越高。然而“同性恋”三个字每次都让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察觉地一顿,突然低下来。虽然一瞬间的迟疑很快就会被滔滔不绝的后话淹没,但这个细节却屡屡出现。
2003年他向媒体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此后一直保持着雄辩的姿态。“同性恋”三个字所带来的表达不畅,是原来隐秘生活唯一的后遗症。周丹承认,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讨论“同性恋”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
“今天我和你在咖啡厅里谈同性恋问题,几乎没有顾忌,但10年前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他环顾四周,满脸堆笑——正如他的观察,周围没有人对他的高谈阔论表示关切。“我们在提篮桥的花园里向经常在那里活动的老年同性恋者做一些医学方面的宣传,发放安全套,谈同性恋问题,周围活动的其他居民也没有激烈的反应,大家能够和平地共处。”
“中国同性恋从‘《东宫西宫》时代’走到了‘互联网时代’”,周丹说。《东宫西宫》是根据作家王小波的剧本拍摄的以中国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前者是隐秘的,孤独的,属于厕所、浴室、公园的偏僻角落,后者是开放的,群体的,属于互联网和大众传媒。
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周丹引用纽约州立大学教授David Greenburg的著作《同性恋的建构》的观点说,美国出现同性恋解放运动时的社会环境,至少四点与今日中国社会环境的相似:稳定的经济发展产生乐观主义的流行文化,酒吧、公园和娱乐场所为同性恋亚文化的产生提供土壤;容易受流行文化影响的年轻人大学入学率提高,将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整体上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媒体的发展。
“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他乐观地说。同性恋已经变成了流行文化隐秘的部分,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贺岁片里。周星驰的《功夫》里有一位穿红色内裤的“兔子”房客;《天下无贼》里劫匪是个娘娘腔;《韩城攻略》里梁朝伟自称被任贤齐抛弃。在搞笑和戏剧中,同性恋比较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中国人表达同性恋的特有的隐晦的方式。
但他本人仍受到大学生的质疑:同性恋公开活动会不会改变异性恋的性取向,使他们变成同性恋?他解释说,过去绝对强势的异性恋没有使少数同性恋的性取向发生变化,反过来又怎么可能?这是个有争议的答案。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厌恶、恐惧和仇恨,不可能通过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人群中极少数人的亮相而得以改变。”
但他仍认为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我每天搜索关于同性恋的汉语新闻。2005年每天都有,从没间断。”媒体已经向同性恋话题开放了空间,孙中欣的课程则打破了大学“通识教育”阶段的沉默。
同性恋的中国语境
不止周丹一个人感到讨论同性恋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危机受到了高度重视,这是中国同性恋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孙中欣说。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所言,“艾滋病防治”这个卫生体系中话语在全世界都已被高度政治化,它使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问题和人群:卖血、吸毒、性交易等等浮出水面。同性恋的中国语境也是在此环境中发生松动的。男性同性恋者作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开始常常在各种“防艾”的会议上被提到。中国同性恋问题开始超越不大的学术圈子,在公共空间里得到讨论,最后被纳入艾滋病防治的整体思路。
“男性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而中国的很多同性恋者为了掩盖身份,都有正常的家庭,这就使他们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一个桥梁人群。”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教授说,学术界和卫生部门不得不开始关注同性恋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要防治艾滋病,就要对这个人群进行行为干预。
越来越多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被吸收到了艾滋病防治的体系中。“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行为干预,根本要依靠同性恋者本身。”周丹说。他本人就是一个例子。除了演讲,他还在同性恋酒吧和公园里进行行为干预:发放安全套、讲授知识。不久前,他还协助上海社科院HIV/AIDS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起草了一份关于上海防治艾滋病的专家建议稿。
但周丹和孙中欣都表示,同性恋问题如果一直捆绑在艾滋病的语境下,无助于改变异性恋者的某些刻板印象——“奇怪的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