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推荐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啦!!!
宋体; 为了解男性人群对尖锐湿疣疫苗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我们拟对男性人群展开此项调查,以为开展后期的尖锐湿疣疫苗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一般情况及对尖锐湿疣疫苗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全程采用匿名形式。调查不会对您的健康和隐私造成伤害,同时我们保证对调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问题,给予严格保密。
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红包啦!!!
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动动手指头几分钟就能领取红包啦!!!
宋体; 为了解男性人群对尖锐湿疣疫苗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我们拟对男性人群展开此项调查,以为开展后期的尖锐湿疣疫苗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本次调查,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一般情况及对尖锐湿疣疫苗相关态度和行为情况,全程采用匿名形式。调查不会对您的健康和隐私造成伤害,同时我们保证对调查中所有可能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问题,给予严格保密。
用手机扫描下面二维码就可以领取红包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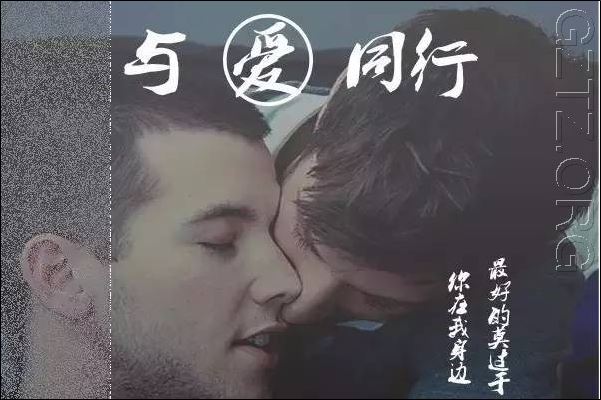 活动:与爱同行
活动:与爱同行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十年来,同志在追求什么样的爱情十年踪迹十年心
有过激情,有过热情,也有过天真的承诺
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隐于市
有人和伴侣接受了开放关系
有人结婚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数人分分合合
还在爱情的旅途中寻寻觅觅
十年,数着很长,过着很短
十年后,爱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要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 谈起性和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SEX-HEALTH图片大赛”正火热举行中哦!
谈起性和健康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现在的“SEX-HEALTH图片大赛”正火热举行中哦!
把你的想法注入到照片,图画,设计(图片或文字)与我们分享吧!
本次大赛将会给大赛前三名颁发奖励(第一名的奖励是iphone6一台,第二,三名将会有惊喜奖品)!
想了解详情请点击http://www.seshglobal.org/sex-health 《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8月初的一天,深圳连降暴雨,但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内却是人头攒动。来自香港的张锦雄Ken仔(以下简称Ken仔)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发表演讲。倘若不是Ken仔自曝,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是个艾滋病人,并在18年前因此而濒临死亡。
栏目更新
- 2015-12-04小S牵线蔡康永 揭娱圈同性恋秘事
- 2015-12-04前10月粤新增"染艾"者5866例 男男同性性传播快速上升
- 2015-08-18性侵同性纳入强奸罪你支持吗?
- 2014-12-19【资讯】李银河谈第二春:爱还是比性更重要 性肯定也有
- 2014-12-19【资讯】性学家李银河回应"拉拉"身份曝光:这不是出柜
- 2014-12-19【资讯】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 李银河谈相伴17年同性爱侣
- 2014-12-19【资讯】李银河谈相伴17年同性爱侣
- 2014-11-20【出柜】孩子出柜该怎么办? 8位妈妈亲述孩子同性恋真相
- 2014-04-09【视角】商院案例:中国同志产业观察
- 2014-04-09【资讯】李代沫身高190cm 曝李代沫颓废囚服照 瘦削如柴无表情
- 2014-03-28【养老专题】同志养老问题
- 2014-03-28【养老专题】同志养老的不能承受之轻
广州:艾滋病感染率升至7.4%
(作者或来源) GT亲爱的网友评审:
本站讯 在本月召开的广州市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广州市男男性接触人群的HIV感染率由2008年的5.2%上升至2010年的7.6%,这意味着,截至2010年年底,广州市每13位男性同性恋者中,就有1人感染了HIV病毒。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卫生部门专家及广同网等男同志社区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据悉,监测流行病趋势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日常政府职能之一。疾控专家表示,感染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感染源增多了,因此病毒在社区内扩散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社区整体感染率就会快速激增。2011年上半年已录得飙升的感染率,某些细分群体超过20%,到年末全市平均感染率或将超过15%.
与会者主要观点摘录
钟菲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生
 感染率会继续上升,并且会上升得越来越快。
感染率会继续上升,并且会上升得越来越快。
关注和判断男同社区中疾病传播的情况是我的工作,为此我们每年都做各种研究。其中有一种是这样,要找100个男同志志愿参与。在年初,这些人都是没有感染的。这两年就发现,到年尾时,同样的一批人中,就发现了5到6个人感染了HIV。这让我很难过。
我发现上网的男同,感染的情况还相对比较稳定,我相信这和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更丰富、更会保护自己有关。有的细分群体就很不乐观了。在那个群体中,我们发现了严重的感染情况。我很想帮助他们理解艾滋病,但我感觉对方的眼光是放直的、呆呆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交往的朋友其实会来自不同的细分群体,疾病因此会交叉传染。所以,一个细分群体中严重的感染状况,也会很快影响到上网的人。感染的人越多,蔓延的速度越快,所以整个社区会越来越危险。
广州的情况和全国大城市的情况都差不多,需要社区的朋友们和我们马上一起行动,保护现在的社区。像西部某个大城市那样,已经超过25%的感染率了——那不是我们要要的。
亨利·菲舍曼 (Henry Fisherman)
旧金山市卫生署 医生
 社区中的所有人需要联合起来,达成共识。
社区中的所有人需要联合起来,达成共识。
我们卫生署相当于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一件事情不太一样——我们这里的帅哥比较多,比例远远高过美女。另外,如果你特别介意我们单位谁是GAY,你应该这样来打听:谁不是。
言归正传。要知道,对一个没有感染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感染的人发生关系,而是和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的人发生关系。因为他不知道,所以玩得时候会更无顾忌。对吗?
旧金山市大约有30%的人是感染了HIV的。旧金山的男同社区,参加定期检测的人大约有70%。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的人,不再需要参加定期检测。这样看,几乎所有的Gay都达成了定期体检的共识。这样做,不仅保护了社区中的其他人,反过来也是间接地保护自己。
广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我真的不希望广州的在感染率上超过我们。
李小米
岭南伙伴社区中心 LGBT权益及友好者负责人
 披露感染率是为了保障公众和同志社区的知情权。
披露感染率是为了保障公众和同志社区的知情权。
我认为在传媒上披露感染率情况没有错,因为兑现对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群体的知情权没有错。逃避艾滋病无异于掩耳盗铃。海外LGBT人群经常说一句话,叫Silence=Death。它可以有很多含义,我的解读是:不大声说出来,大家就一起去死。
艾滋病问题特别麻烦的地方,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物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社会病。比如,艾滋病很容易触痛一些人的道德神经。
前两年,东北一个地方的疾控官员教小姐用安全套,媒体披露后,掀起了轩然大波。2009年我们首次在广同披露感染率数据,也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安,有的人认为广同“家丑外扬”、“制造恐慌”,加重了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图谋不良。
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它与人们的道德观密切捆绑,偏偏某些道德观未必科学和理性。当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复杂程度时,大家都不太敢讲话了,因为怎么讲都会错。
我们的社区所存在的问题,是道德观念落后的问题。让大家知情,虽然可能会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减少愚昧的最好方式。
小藤
广同网 社区服务中心 /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社会学在读硕士
 艾滋病就像职业病,及早治疗好过讳病忌医。
艾滋病就像职业病,及早治疗好过讳病忌医。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歧视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歧视比如我在上下班高峰抱辆自行车去挤地铁,周围人不解、嘲笑的眼光是一种歧视。另一种是自我施加的歧视,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其实别人也没对你怎么着。
我在法国经历过浩浩荡荡的同志大游行,终点在巴士底广场。游行的最后一幕,所有人齐齐躺在地上,纪念因艾滋病死去的人。参与其中和做为旁观者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这时候,才感觉到艾滋病也可以去除歧视的标签,作为患者,也可以接受它,积极治疗,健康生活,和它一起存在。
国内的氛围就很不一样,在艾滋病问题上,我们同时面对着外来的和自我施加的歧视。在外来的歧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努力消除对自我的歧视。男同是易感人群是正常现象,有生物学上的直接证据。在国外,同性恋社区不在将艾滋病问题视为公众强加的阴谋,在自豪和获得尊重的环境中,能够把艾滋病视为职业病一样淡定的态度,因此获得最大的抗击艾滋病的能量。艾滋病在男同志中高发,全世界都一样,这是事实,不能回避。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感染者,第一眼见到他时,就被他的气场震住了:白色衬衫牛仔裤,颜色分明,给人一种正直、清爽、阳光的感觉;眉宇间透露出友善,让我觉得我们是已经认识多年的好友。当他知道我独身一人到旧金山的时候,非常热心地给我安排旅游路线,并介绍他的一群好友给我认识,其中包括他BF.相处中我得知他和他BF在一起已经7年,并且还是大家眼中的最佳情侣。
临走的时候,他的朋友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幸好他(感染者)有定期检测的习惯,及早发现自己感染了,不然AIDS将会很快夺走他的生命,我们就会少了一位如此好的朋友。”
当时我们是在一家有点嘈杂的酒吧中,但我每个字都听清楚了。他们从未提到“为什么他会感染?”、“肯定是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之类的话。
冰冰
岭南伙伴社区中心 艾滋病教育项目负责人
 心态变化促使更多同志主动定期参与HIV检测。
心态变化促使更多同志主动定期参与HIV检测。
我这些年都在张罗在广州社区提供检测服务的事情。现在,周末来我们中心做过检测的人已经接近五千了。
有一次,在我们这里做完检测的朋友,回到我们中心。他告诉我他拿到结果,证实感染了。他在沙发里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我知道他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陪着。
这种情况很常见,有上百个人回来找我们帮忙。坦率地说,广州的人太多了,这让我们十分忙碌和疲惫,但我感觉大家喜欢和信任我们的服务。
我感觉,相比之前,现在形成定期检测习惯的人多了很多。我有时会和来检测的朋友聊天,当问到“你为什么要来检测”时,我听到的“我已经习惯了”的声音越来越多。以前,更多的是“因为我担心自己有可能感染了”。
从因为担心、所以检测,变成了因为对自己负责、所以检测,自觉的人多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我们做的一个调查中,发现定期检测的人都有以下品质:习惯自己拿主意的、经济上比较独立的、外语较好的、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业余爱好广泛的。我认为,越独立的人、越会照顾自己;越会照顾自己的人,各方面越独立。所谓靠父母、靠朋友,不如靠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良好的品质。
编辑寄语
黄海涛
中山大学/广同网 特约编辑
 我们需要持续反思。
我们需要持续反思。
很多人都知道的所谓三大人群(吸毒、母婴、性)最容易受到艾滋病影响。但是,当老百姓接触到这些概念,尤其是与“性”有关的概念时,会因为某些陈旧落后的性道德、性伦理和性观念,把艾滋病视为一种道德病,从而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产生歧视与排斥。
性在多数人眼中不是什么好东西。得过性病的人,没有几个会和朋友坦然地说自己得过性病。因为普通人很自然地把“性乱”和“生病”联系在一起,同理,艾滋病也被扣上了沉重的道德大帽子。而事实上,在现代医学条件下,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已能大大延长,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艾滋病已被社会公众视为一种慢性病。
而在医学临床实践和大众传播方面,翻译的失误也导致了歧视的加剧。所谓“高危人群”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易感人群”(highly vulnerable)。患者和感染者不是“毒王”,他/她们是病毒的受害者;更是歧视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文化的受害者,理应受到关爱和平等对待。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逐步消除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歧视。
而在同志社区内部,我们必须承担起责任——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负责,并且努力消除社会公众对同志人群和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的偏见。同时,同性恋者必须意识到,在歧视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免于歧视的孤岛,我们还要消除对社区内部“自己人”的偏见,以及对社会上其他弱势人群的偏见。
意识到以前的理解存在偏差的时候,就应该采取行动去改变它。面对年复一年披露的并不让人乐观的男同志HIV感染率和感染人数,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担责任,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会的成见埋单。
亲爱的网友评审:

